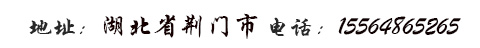天目物鸣录
|
治白癜风多少钱 http://m.39.net/pf/a_6562617.html 韩育生 笔名深圳一石,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甘肃小城秦安 现居北京,作家、自由撰稿人 从小熟悉山野田间的花草树木 在古典诗词中感受万物的鲜活灵动 在美、性灵与感动中寄寓现实之外的人生 已出版作品: 《美人如诗草木如织——诗经里的植物》 《香草美人志:楚辞里的植物》 《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情怀:草木笔记》 《采采卷耳:诗经草木魂》 [静处喧腾] 早晨六点,疾步走过寒风,即日立冬,便下意识在路边草茎的水珠上寻找霜花的印迹。 很少早晨六点起床。飞机上随手翻开《中国野生植物图鉴——古田册卷》,没读几页,人就昏昏沉沉跌到梦里,梦里没见到即将要去的山水江南,气流把人颠醒时,朦朦胧胧的意识深处,梦里脚步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。无神的看着云海造山峦,身体像水一样流得空空如也,突然感觉到一份说不出来的失落。 萧山机场和朋友汇合时,潮潮的空气,衣服几乎贴着身体发热发粘,呼吸一时都要被黏住。一路上人烟是雾,车道两旁苍翠的柳杉林是雾,水杉潮潮的褐色羽叶上是雾。知了酒店房屋的窗外,杉木高耸的树身从阳台上伸出来,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诱惑。世界绵延,山林试图拥抱,人迹、鸟兽、虫鸣、车流一时隐在雾里消失无影。 晚饭后,和茜公子走过禅缘寺周围漆黑的森林步道,手机电筒的光芒照出直直的一束,无数雾的颗粒在光里如浮沙一样飘落,好像深远的山林深处正有另一个世界,在我们眼前阻隔出我们正试图走入的空间。此行的目的或有这样的一份企图吧。吃饭、喝茶时大家聊起的山林、自然、生命话题的延伸,在细雾和夜色深处都变成流淌的小溪,流经山脚不远处的小溪,打湿泥土里的枯叶,带走浮生幻灭的鱼影虾衣,雾珠的晶莹,将人的意识留在敏锐与朦胧的交汇之地。回房间里,想整理一下思路,为第二天的采访把一些主题的脉络整理出来。 山水的幽静反倒容易让人困倦,睡下时,梦里尽是《诗经》里故事的影子,相隔两个小时会醒来一次,内心说不上来的平静,仿佛此刻自己的身体贴近了山林的肺腑。采访的事总是占了心里一块。梦里好多未尽之事的喧腾,早晨六点醒来,全无睡意。第二天对着摄像机镜头,到失去一些平常聊天的自如。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摄像机,试图把握,试图放松,反而让人更加僵硬。采访时,天目山的雨意在窗外越发热烈,击打着阳台上白色的桌椅和深褐色的木条。真想站在细雨中,雨意飘洒,湿淋淋的冰凉,讲述起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中“依依”的深情,“霏霏”的敏慧,定会别有滋味。可惜,雨势大的让人收回了户外的想法,只能枯坐在椅子里,内心的诗情反而蜷缩着,被干巴巴的语言卷走。艳坤诱导我讲述自己的写作历程,诗的世界渐渐打开了一面,慢慢的,我也忘了自己正坐在镜头前。 [贴近幽魂——见芒] 诗到现场,这种痴念一直是我写每一种《诗经》植物的妄想,这种妄想让呈现远古诗意的场景显得虚无。 与芒草突然相逢,意味着偶然与必然同时在眼前展现。心中结了许久的执念,在花、叶、径脉的抖动和摇摆当中凝成一团一团雪花的喧闹,透过天目山常年云雾笼罩难得散尽的天空,芒草花上疏散的白羽,就像蓝色火焰内部深层安静的留白。花上半透明的白光,一瞬诱惑了我。 车在下山坡道上飞驰,就在短得难以察觉的片刻,车窗口几道一闪而过的光束,刚好照透道路拐角几丛芒草疏散的花束,花束原本低沉的土灰色,在阳光里完全化为雪的半透明的质地。那种由土灰突然变为洁白的华彩,惊得眼睛一跳,“原来这才是芒草被称为白华的原因”。 几周前,坐在首都图书馆里写芒,当时并未见过大自然的芒究竟是什么样子,为此,脑海里开始跋涉一道道的幽谷,寻觅芒草何以称为白华形神兼备的魂魄。图片上芒草苍灰的影像呆呆滞滞,怎么看都触动不了“白华菅兮”(《小雅?白华》)的诗意。想写而不得,只能一次次眯起眼睛,看眼前书脊、人影朦朦胧胧的线条,想象一份哀怨如何一点一点显出温柔,想象一个女子(被废黜王后身份后独行空屋的申女)试图为走出情爱樊笼和时空阻隔做着武王的努力,想象她见芒而生,自比白华的心境里无法疏解的哀伤,想象一个痴情人如何在一份永失的爱里重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想得越多,笔底到越发苍白起来。 诗句中间流淌的不安熄灭的爱的意志,是藏在诗人心里,还是被白华(即芒草)的身影所承接和安慰了?心头的这个疑问总像一个谜。车从天目山山顶奔驰而下,飞过竹海,飞过柳杉林,飞过秋意浓得化不开的山脊…… 我怀抱背包,蜷缩双膝,眼睛不时看到自然与时间之外。初见白华的诧异不时占据身心,心里流动其一股无声的暖流。很奇怪,真正看到芒草转换为白华的秘密,越是身在诗的神秘与物性神奇对接的现场,诗的世界从内心里呈现出来的图画,那么鲜明真实,《白华》诗意的迷人与神秘到更难以说清。这种难以说清的感受,似乎净化并推升了《白华》对艺术感受的意义。 申女内心的孤独,这白华在眼前闪现出来的影子,幽魂一样,从诗中一角的芒草身上,隐藏了生命从一份灰暗变为洁白的孤独,这孤独似乎超越了,又似乎永远都无法超越。《白华》的愁怨里,是否还有一个人睁开双眼看向自己内心的悲喜哀愁? [竹林狗] 无聊总是独特,它能让人感觉到时间的枪口抬起瞄准你。无聊的子弹射中一个人时,最初的感觉总是倦怠,昏昏欲睡的洞穴似乎一时要成为防空洞一样的避难所,之后,生命的无意义在意识的软肋上猛地一刺,便又要寻些比此刻更为有趣的事情,当做保持身体活力的坚盾、利矛。 森林里的阴天,阴冷来的总是出其不意,从树海深处涌出,在湿得滴水的青苔上袭向人。高耸的柳杉、水杉褐绿色的树影栅格中间,大雾穿行,软绵绵的白雾,软玉一样打湿翡翠般精巧的羽叶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山野之梦的碎片不断编织的魔力,同时也在人的心头编织。 天目山半山腰的竹林隐在云海里,风动山行,车如船行浪中。云中夹带的雨,一时下,一时停。在“大地之野”的休息室,屁股一碰到椅子,就有一种与睡梦神相遇的错觉。只是不想睡,便拿了雨伞,出门去山野闲游。大门外的车道上,雾中世界安静极了,四周隐约有水涛声竹鸣声一阵阵传进耳鼓,声音敲打,似乎要把人心头的别离遇合一齐唤醒。一路上,眼前飞掠而过的毛竹海、山核桃、东风菜、蒲儿根、山柿、博落回……的影子,这个时候全都散进雾里。 雨欲停非停,空气潮而冷。门口大道对面,靠着竹海山林的沟渠边,几丛鼠麴草的小黄花和野茼蒿弯着头的橘红花,花儿在岩石缝隙的土台上开的鸡零狗碎。山林的冷寂似乎更易催逼出胃的饥饿感,看着花儿,想到的是青团(鼠麴草是制作青团的原材料)的软糯、野茼蒿肉片汤(曾在广东韶关一带吃过山民用野茼蒿做的肉片汤)的清香。 俯身拍照,细小微弱的花魂在色彩和节气的构图中定格,每往花儿的生命深处看,总有种琢磨不定的气息在画面上游走。花草树木吸引我的一个原因,也正是这种琢磨不定中跳动的神秘歌韵…… 拍照时,身后传来的唰唰声并未让人注意,抬头盯着花时,到是一惊,以为野茼蒿的花朵叶动还了魂,花朵背后突然多出了一双黑漆漆的眼睛。在镜头深处,一头激动不安的小花狗的脸,它眉目中间盯着镜头的友善,让人揣摩不定。“啊!”我一下子直起腰来。小狗的眼睛显然并未躲闪,它似乎懂得我很多,正等我伸手去抚摸它的头顶。我呼应了它的期盼。一瞬间,一人一狗初次相逢的陌生感消失的无影无踪。 我继续沿着路边行走,寻找11月的山野上陌生有趣的花草。盛开的飞蓬,高昂着头竖立在阴云底下的芒草(可能是五节芒)……找到几个深海海葵一样的硬皮地星时,想与人分享一种新奇生命的念头让我停下脚步回头四忘。大路上,竹林里,不见人影,只有脚下跑来跳去的小花狗,极力想要明白我目光里的心意。 竹林斜坡敞开的一个豁口处,一棵白山茶上零星的几朵白花挂在枝头。白山茶的花儿诱我朝竹林深处探着头望。还没决定是否深入竹林,小花狗已经箭一样窜进竹叶中间,几个转身就在竹林深处不见了踪影。竹林中间颇有些曲折的之字形道路,道路两边,看到多种堇菜的绿叶,看到斑叶兰精致的叶瓣上的脉纹,看到寒莓熟透的果实张开美艳的嘴唇…… 转过一个之字形拐角,天空突然一亮,竹林开出一个天窗,小花狗正从一颗南天竹橘红的叶子中间朝我站立的地方直冲过来。它在我的眼前急刹住,动作洒脱,我蹲下身,想要去拥抱它冲过来的那份冲动,它却从我的双手中间一下子跳开,跳到落叶深处。风里发黄的竹叶飘飘洒洒落下,雨珠打落肩头。 飘洒的竹叶,竹林里的一只狗,孤独单单一个人,此刻,倍感一种写作时常有的那种欣悦与平静同在的孤独感。独自站立的片刻,一狗一人,似乎都明白了自然的荒野之中超出视域之外的一些东西。 [遇枳椇] 阴云严严实实盖住了林中早晨,同时也就盖住了时间的流淌,若说那个时候是中午,是下午,感觉都差不多。雨在绿森森的柳杉顶上悬着,就是俏生生地悬着。要不要落,怎么落,似乎都凭头顶云中人的爱憎喜好。天目山的雨真像捉摸不定的女子心。 在“自然学校”门口汇合,艳坤、吉木、茜公子和我,我们等着坐景区班车去天目山(属于西天目)山顶,在门口动植物展示台上,见到不知是谁摘来的一束枳椇。 当地应时成熟的佳果,我和枳椇初遇算得上是巧得不能再巧的缘分。几天前还在首都图书馆里隐在《诗经》世界里,读《南山有台》,写枳椇,想木蜜(枳椇的一个俗名),驰骋想象力飞翔,听到的全是古人的画外音。 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臺》里写到“南山有枸,北山有楰。乐只君子,遐不黄耇(gǒu)。乐只君子,保艾尔后。”大概意识是:南山长着茂盛的枳椇,北山长着繁盛的鼠李。有德的君子,一定会延年益寿。有德的君子,他的后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。 古人对枳椇的名称、形态、价值都有过详细的描述。最早的《毛诗故训转》:“枸,枳枸。”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:“枸树高大似白杨,有子著枝端,大如指,长数寸,噉之甘美如饴。八月熟。今官园种之,谓之木蜜。” 《本草纲目》卷三十一释枳椇:“枳椇,果实名木蜜、木饴、木珊瑚、鸡爪子。木名白石木、金钩木、交加枝。”枸树树枝多曲,其子亦卷曲,故有枳枸之名。曰蜜,曰饴,因其味也。曰珊瑚,曰鸡爪,象其形也。 《本草纲目集解》:枳椇木高三四丈,叶圆大如桑柘,夏月开花。枝头结实,如鸡爪形,长寸许,纽曲,开作二三岐,俨若鸡之足距。嫩时青色,经霜乃黄。嚼之味甘如蜜。每开岐尽处,结一、二小子,状如蔓荆子,内有扁核,赤色,如酸枣仁形。飞鸟喜巢其上,故宋玉赋云:枳枸来巢。 《周礼·曲礼》:“妇人之挚,椇、榛、脯、脩、枣、栗。”意思是说,女人相见,相互赠送的礼物是枳椇、榛子、果脯、长条肉干、枣子和栗子。可见枳椇在周朝,已是送礼的重要干果。 宋玉《风赋》:枳椇来巢,空穴来风。枳椇又为成语“空穴来风”的源起。枳椇俗名拐枣、峦字梨、甜半夜、梨枣树等,经霜之果,味道更为甘甜。 枳椇是鼠李科枳椇属落叶乔木,树身能长到25米。花期6月,果熟期10月。分布于黄河中下游,是中国特产。树皮、木汁、叶、根、果实、种子均可药用。木材软硬适中,纹理美观,不易反翘,是做家具、车船、微细木工、装饰工艺的良好用材。枳椇树冠优美,是做庭院树的好树种。 大家分食我们的先人引为君子的果实,枳椇的果实里,混合着苹果的清幽、蜂蜜的香甜、还有一股木质包裹着果实的草木味。想象古人还有枳椇酿出甘甜的美酒,“木蜜”两个字不在只限于纯美的现象,还有一股源初亲近山林的诗情,与自然相融一体的亲切,让人理解到几千年前人们爱一种果实的激情。接下来的几天,始终没有机会见到枳椇树,没有在长满果实的大树下面站上一回。 [幻住与幻不住] 天目山山顶的云雾,经风一动,骤冷即成雨雨不像很大。走在山道上,用这样的心理安慰自己,是希望能在细雨中拍一些适用的镜头,也算是这个时候正好完成登顶西天目的任务。 天目山原生态的绿色保护的非常好,走人其中,并无多少过度开发的痕迹。晚上所住的知了民宿,全然像是森林里安静、整洁、舒适的鸟巢,房子就像架在柳杉和水杉的半树腰上。年跟着北京自然之友植物组来天目山看植物,那时候听朋友说,天目山的植被保护的比黄山还要好,自己的亲身体验,一路上的修竹、清流、深树和盛开的花草,都暗合了南方山水“秀丽”的名声,我所感觉到的是温和的清丽与深秀。 雾起的山林,让我想起山顶路边盛开的杜鹃花,在《给孩子的神奇植物园》里所写的天目杜鹃的现场,就在半月池旁凹进路旁的山崖边,那里有我与一束雨中花惊心的相遇。 山石路面开始湿滑,雨声一时赶着一时,似乎要把人赶到避雨的地方。雨丝遮掩的幻住庵(现在叫幻住山房),站在高处台阶上,能看到竹林掩着一个院落几间瓦房,完全没有庙宇禅房的幽然气息,更像是烟火人间开垦出来的一方田园居所。雨丝冲洗着小小的院落,院子里的石头泛出清冷的光。说是幻住庵,艳坤说这里正要整理成一个文人墨客浸染其中的书房,让我更喜欢这个“幻”字深处的书卷气。 幻住庵有两个终年在庵里工作招待客人的女子,热情地为我们泡茶,询问着准备午餐。庵里布置的像一个茶室,木椅,八仙桌,桌上写意的斗瓶里有新插的插花,叶、枝、果都显出一种极简的写意的美。中堂有中峰高僧的画像,证明着幻住庵主人试图托起整座苍山的思海里的气势,看着画像两边,有他如疾风裂岩一样的笔峰写成的字迹,这些字迹与幻境到有一种迷思般的结合,和侧面他的孙字后辈,大书法家赵孟頫写给叔祖俊逸、圆满、均衡的字迹相比,中峰和尚心灵的动荡显然让幻住庵变得不同寻常。 时值11月,雨中的山林里,湿气渗出的丝丝寒气,透骨凉。看到客厅墙角一个红彤彤的火盆,让大家一时欢喜,心里生出一个不知何来的想象,或许这正是幻住庵的这个幻字的魔力——幻住心不住。远离尘世的嘈杂,安静自守一份心灵幻念,三两知己围炉夜话,今人与古人举杯。这些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场,并不是一种想象,而是随雨意浮云,聚拢过来。 我们考着火盆,喝着白茶,聊着天,吉木和茜公子拍兴大起,到处拍个不停,我偶尔到门口看看雾与雨的交变,数一数院子里石头桌面上雨点环纹的大小。家常的午饭,凉雨云雾中苍山顶上的火盆,这些让人的胃口似乎开了不少。 饭后没多久,吹来一阵风。雨刚停,站在幻住山房门口的台阶上,看流云的白纱在眼前的绿叶和水珠上飘动,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,微微轻暖,天目在眼前微微睁开碧蓝深眸,那种惊变,恍然让身边神秘的变幻引得心神飘忽。 很奇妙,吉木让我看他刚刚在雨中拍到的柳杉大树影子里雨点的环纹,镜头里,环纹的涟漪,银河一样深邃,禅语偈言一样悠远。路边随处可见胸径一两米的钻天的柳杉,虽然不及北美红杉惊人的上百米的威压,但吉木让我站在树下拍出的照片里,我就像树影深处的一只小小甲虫,随时会便山林一声轻微的响动淹没。 阳光在树皮厚厚的青苔上褶出光与影的皱痕。整个山林因为从雨中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的照射,小鸟、绿叶、水流都好像新生儿的翻滚,进化和沉寂积压在它们身上的幻灭,一时从迷雾里消失。那种醒来的感觉里,鸟儿穿雾鸣叫,阳光照进青苔,水流沿山石罅隙流进万物心里。 幻住山房的招待人员说,这样的天气是天目山山顶的常态,但就在几个瞬息中间,云雾、细雨、阳光各自变出一种别样的世界,让观想之境、梦中之境、现实之境几乎同时推到眼前,这样迅疾的变化让人恍惚,人生意义的宝塔里,有多少重是真念,有多少重是假想。 文字_韩育生/摄影_吉木 图片未经著作者许可,任何媒体、个人均不得随意转载、复制, 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-END- 摄影、电影、文字的集散地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ongqisx.com/hqcb/1079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昆明优质鲜花批发价5月11日
- 下一篇文章: 昆明优质鲜花批发价10月5日